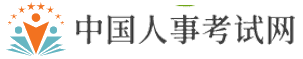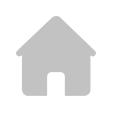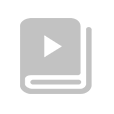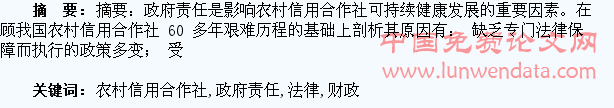
摘要:政府责任是影响农村信用合作社可持续健康进步的要紧原因。在回顾国内农村信用合作社 60 多年艰难经历的基础上分析其缘由有: 缺少专门法律保障而实行的政策多变; 受行政干涉过多而得到财政支持过少; 信用功能不断强化而合作功能不断弱化。同时借鉴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家农村合作金融成功的经验: 及早立法规范,财政大力支持,特殊监督保障。最后提出强化政府责任的有关建议: 加快农村信用合作社有关法律法规的颁布; 政府要加强对农村信用社的财政投入; 政府要旗帜鲜明地强化农信社的合作性质。
关键字:农村信用合作社; 政府责任; 法律; 财政。
长期以来,国内理论界和实践界对于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与进步,多数都是从其自己角度来研究,较少提及农村信用合作社进步中的政府责任; 多数都是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其自己经济问题,较少提及农村信用合作社进步的社会学意义和政治学意义。事实上,现代意义的合作社是克服资本统治弊病构建“和谐社会”的“法郎吉”( Charles fonrier,1843) ,它“以工厂规范和信用规范为起点”,是通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点”( 马克思,1848) 。因此,西方合作社初办时就遭到政府和全社会的高度看重,并通过立法规定了政府责任和财政金融支持政策。
在当代,无论是“合作社的摇篮”丹麦、“今日之瑞典合作社”( Anes J W,1952) 、“在英国工业的合作社与合作中发生的革命”( Young Michael,Mar|ianne Rigge,1983) 、“意大利的合作社运动”( LloydE A,1925) 和“美国的合作社: 为收益而耕耘”( Kansas City,1994) 、“市场所作社和金融结构: 经济剖析的买卖本钱”( Hendrikse G W J ,Veerman CP,2001) ,还是“来自法国的证据”( Estrin Saul,Derrk C Jones,1992) 、“参与政治、组织民主和以色列基布兹的经验”( Rosner M,1983) 和“国际合作社网盟关于合作社特点的申明”( 1988) ,西方国家的合作经济进步都有法制保障和明确的政府责任。在东亚,无论是日本农业“协同组合”,还是韩国的农协和中国台湾的农会,都被视为综合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要紧组织形式,同样都有法制保障和明确的政府责任。
党的十八大报告和 2012 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民合作社”( 自然含“农村信用合作社”) 进步提出了新的思路,更多地强调了“农民合作社”进步过程中政府的责任。
1、国内农村信用合作社进步的艰难经历及缘由剖析。
国内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主体,是支持“三农”进步的主力军,但从其成立到今天 60 余年可以说是屡经曲折、步履蹒跚。从1952 年贵州桐梓县成立的第一个农村信用合作社,至 1958 年的农村信用合作社,都主如果由农民( 社员) 集资组建而成,比较充分地体现了农民个人所有制基础上的合作性质,但几乎没政府财政支持。
1958—1978 年,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权先后三度被下放,又两度收回。过度的政府干涉使农村信用合作社渐渐偏离“合作制”的进步轨道,成为政府的附属物,走上了“官”办道路。
改革开放后农村信用合作社有较快的进步,1984年国家决定恢复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三性原则”( 组织群众性、管理民主性和经营灵活性) ,但并没突破国家银行管理的框架,管理体制没实质性变化,民主管理流于形式,改革非常不彻底。
1996 年,国家需要农村信用合作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农村信用合作社开始向着“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合作金融组织方向迈进,越来越摆脱了进步缓慢、连年亏损的不利局面。但随之而来的盈利水平偏低、业务风险较大、服务日渐商业化等一系列问题使农村信用合作社陷入紧急困境。纵览农村信用合作社 60 余年艰难的进步经历,几度改革都不深入,几度回归“三性原则”都不到位,其缘由是深层次的。
( 一) 缺少专门法律保障而使实行的政策多变。
自国内农村信用合作社成立以来,国家拟定了一系列有关草案与条例,但这类政策多变不定。
1951 年,中国人民银行下发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章程准则( 草案) 》规定信用社的性质是农民我们的资金互助组织; 1962 年 11 月《农村信用合作社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明确信用社是国家银行的助手;1993 年《国务院关于农村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又明确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国内政府几乎每年都会在中央有关文件中对农村金融机构进步提出需要,说明国家对农村信用合作社很看重。但国内到今天还没专门的《信用合作社法》,没从权威的法律角度规范和引导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营运管理。因为缺少健全的法律规范作保障,农村信用合作社没办法可依的情况紧急妨碍了其合理化、规范化的可持续进步。
( 二) 受行政干涉过多而得到财政支持过少。
《深化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策略》明确需要省级政府不干涉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具体业务和经营活动,但不少地方政府把农村信用合作社当成是地方政府的筹资工具。多年以来,地方政府长期占用农村信贷资金,甚至很多负债于农村信用合作社,这紧急威胁到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安全运转。尽管国家一直强调农村金融机构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但适合的权力下放并没解决根本性问题。农村信用合作社一方面承担着服务三农的社会责任,并一直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信贷支持; 其次还要吸收特种存款,购买上至中央下至地方的各类政府债券,却并不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因其合作金融的性质而享有相应的打折政策。相反,国内财政舍弃了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财政补贴,其税金、筹备率等与一般商业银行并无太大差异,再加之农业生产具备经营风险大、ROI低等特征,农村信用合作社一直面临着较大的信贷风险,其进步遭到了政府财政支持过少的紧急制约。
( 三) 信用功能不断强化而合作功能不断弱化。
国内农村信用合作社在成立之初产权基本上是明晰的,是打造在农民个人所有制基础上的信用合作,通过社员之间的互助合作,相互融通资金,合作制原则体现较为充分。但伴随改革的进展,农村信用合作社进入了自我管理、独立进步的新阶段,国家对农村信用合作社薄弱的财政支持致使其金融服务日益商业化。在贷款对象上,投向高收益的行业; 在贷款方法上,需要借款人提供贷款担保和抵押贷款,进而抑制了小生产者的资金需要。农村信用合作社这种难以满足农村多层次资金需要的的商业化经营,非常可能致使昔日高利贷信用的死灰复燃。另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1 年 8 月表明其鼓励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为农村商业银行。可见,现在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信用功能不断被强化而合作功能不断被弱化,这种近况是妨碍农村信用合作社健康持续进步的另一个要紧原因。
2、美、日、印农村金融进步的政府支持。
海外农村金融大多经过了 100 多年的进步,很多比较成功的经验值得大家借鉴。这类国家为了进步农村经济和扶持农村金融,都采取了多方面的支持和保护性政策。
( 一) 及早立法,规范农村合作金融的进步。
美国于 1916 年通过《联邦农业贷款法案》,组建了信用合作组织,打造了合作农业信贷系统,专门办理农业长期贷款。其后又不断立法修正,从而使农村合作金融运作有法可依。
日本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是“农业协同组合”的一个子系统。日本于1947 年颁布的《农业协同组合法》,赋予日本农业协同组织合法的社会地位并对其行为进行规范。
印度先后颁布《印度储备银行法案》、《银行国有化法案》、《区域农村银行法案》、《国家农业农村进步银行法案》等有关法案,以立法方法提高机构覆盖面和信贷投放水平。
( 二) 财政出资,支持农村合作金融的进步。
美国政府对联邦土地银行曾两次提供资助:国家联邦土地银行成立时资本总额 900 万USD,其中政府提供 889. 2 万USD;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危机,美国政府再度出资 1. 25 亿USD助其度过难关。美国政府在政策上通过不征收营业税和所得税、不收取存款筹备金、自主决定存贷款利率、打造保险机制等多种打折手段扶持农村合作金融进步。
日本政府对农业协同组织的财政支持主要通过税收规范和直接财政补贴两方面达成。税收方面,日本政府规定对农业协同组织实行低税制,农业协同组织的各项税收都比其他法人纳税税率低10% 左右; 财政补贴方面,日本政府补贴数额较大,补贴方法多样。
印度政府对农村信贷推行利息补贴和信贷免除财政打折政策。政府补贴商业银行及区域农村银行对优先进步行业的贷款打折利率( 9%) 与市场利率之差; 对于 1989 年之前商业银行向农村区域和农民发放的中长期贷款免除其本金和利息部分,政府给予补贴。
( 三) 特殊监管,保障农村合作金融的进步。
美国专门设立了以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为服务对象的农村合作金融监管体系,该体系进步到今天已经比较完善,包含农村合作金融监管机构、资金融通清算中心、行业自律协会和互助保险集团。
日本打造了对合作金融的双重监管体制。政府金融监管厅主要推行对全国各种金融机构的监管; 农林水产部门、农政局、农政部配合金融监管厅推行监管。
印度对农村金融机构推行特殊的监管政策。印度监管机构对农村贷款风险分类特定标准,一般贷款连续 90 天不还视为不好的贷款; 但对于农业贷款根据生产周期考量,一般短期农贷逾期两个生产周期以上视为不好的贷款。
3、强化农村信用合作社进步中的政府责任。
为了国内农村信用合作社进一步迅速稳进进步,突出强调政府责任至关要紧。从海外农村合作金融成功进步的经验来看,大力的、有效的、权威的、多元的政府支持是农村合作金融可持续进步必不可少的砥柱力量。鉴于此,大家建议政府应在以下几方面有所作为:
( 一) 加快农村信用合作社有关法律法规的颁布。
海外农村合作金融进步比较成功的国家大都有专门的法律法规来规范、约束、引导、监督农村金融活动。这类国家立法较早,并且伴随农村经济的现代化进步、农村金融需要的多层次变化,准时修改法规、调整政策,以适应农村合作金融进步的年代需要,切实保障社员利益。国内应尽快颁布《农村金融法》、《信用合作社法》,以权威的、刚性的法律形式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权力义务、资金运作、税收打折等做出明文规定,以此规范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经营行为,保障社员的合法权益。
国内农村信用合作社已经进步了 60 多年,立法条件已经成熟。通过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法律化,增强其权威性,在保证农村信用合作社经营活动公开透明的同时,愈加能够帮助推进其健康持续进步。
( 二) 政府要加强对农村信用社的财政投入。
世界合作金融进步经验表明,政府财政支持是合作金融健康进步的保证。现在,国内农村信用合作社面临历史包袱沉重、经营本钱过高、贷款风险较大、资金运转不灵等问题。因此应该从支持农村合作金融进步的大局出发,在充分考虑农村信用合作社特殊性质的基础上,给农村信用合作社创造好的宽松环境。第一,提供多类型的资金支持。因为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特殊合作性质和特殊金融地位,政府对其改革所遗留的历史包袱和经营本钱,应该给予独立资金拨付,以保证其保本运作; 第二,实行特殊的税收打折。可减免征收所得税和营业税或税率征缴较一般商业性银行减少肯定比率等,以保证其维利经营; 第三,投入广泛的资金补贴。比如对农村信用合作社发放农户贷款低于存款本钱利率的部分,政府应给予利差补贴等,使国内农村信用合作社更好地为农村经济进步服务。
( 三) 政府要旗帜鲜明地强化农信社的合作性质。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简称银监会) 于2011 年 8 月明确提出: “从 2011 年开始,要通过 5年左右时间,达到农村信用合作社股份制改革全方位完成的目的”。这表明银监会官员只看到农村信用合作社的金融属性,而否定其合作制属性的历史和事实。应该说这是值得商榷的,银监会的这一决定,好像颠覆了农村信用合作社一直在农村金融体系中起主力军用途的历史背景。国内中、西部进步相对落后,各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经营进步差距较大,不可以偏概全。对于少数发达区域,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条件成熟的,可以向农村商业银行或农村合作银行转型; 但对于大多数扎根于经济进步落后的中、西部农村的信用合作社,政府应该旗帜鲜明地强化其合作性质。其次,因为有关法律法规不完善、政府财政补贴不充足、政策扶持不明显,农村信用合作社自己营运管理不善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到今天缺少政府财政的“后台”保障。为了自己的可持续进步,农村信用合作社所提供的金融服务渐渐向选择性、商业化过渡,这种情况假如长期存在很不利于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的进步。因此,国内政府应在扶持农村信用合作社进步的同时,着重强化其合作性质,以保持农村信用合作社可持续健康进步。
参考文献:
[1]谢元态。 中国特点的农村金融改革与进步的道路[M]。 南昌: 江西科技出版社,2007.
[2]聂云霞,谢元态。 在国际比较中看国内农村信用社的若干问题及其对策[J]。 农业经济,2001( 2) : 12 -13.
[3]张元红。 当代农村金融进步的理论与实践[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4]张贵乐,于左。 合作金融论[M]。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5]张奎,李泽民,吕峥嵘,等。 发达国家农村合作金融进步改革经验考察、比较及启示[J]。 武汉金融,2006( 10) : 21 -23.
[6]秦秀红。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农村金融的进步经验分析[J]。 安徽农业科学,2008( 36) : 6991 -6992.
[7]胡卓红。 浅析海外政府对合作社的支持[J]。 中国合作经济,2009( 6) : 53 -55.
[8]尤保庭。 海外政府在农村合作金融进步中有哪些用途及对国内的借鉴意义[J]。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8( 28) : 92 -94.
[9]中国银监会赴印度农村金融服务考察团。 印度农村金融改革进步的经验与启示[J]。 中国金融,2007( 2) : 31 -34.